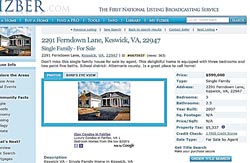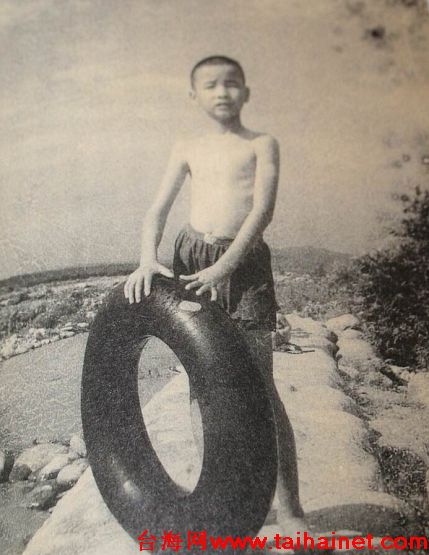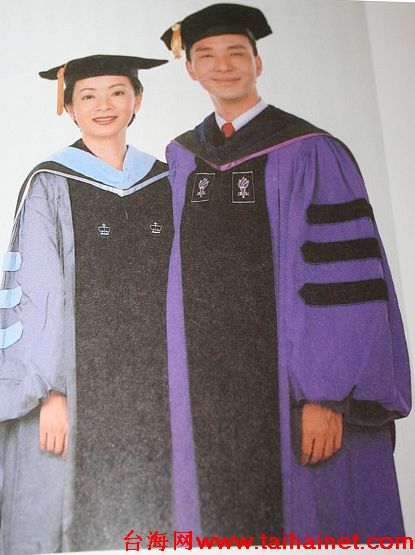“神头”詹学彦(左)和詹家屯三国地戏队部分成员
活跃在“5·28”城隍节上的地戏队
雕刻繁复美丽的地戏面具
贵州安顺地戏现状:官司与乡土
和张艺谋打一场6年前的官司,詹学彦套用安顺市文化局领导的话说,“不赢也赢了”。电影《千里走单骑》里,他带着安顺旧州镇詹家屯三国地戏队的表演,被字幕打为“云南面具戏”,于是有了今年在北京开庭的“正名”官司,以及庭上农民们穿戏服、执大刀指控的一幕。现实中,被学界誉为“标本”、“化石”的“地戏”,对当地人鲜活实用。
记者◎葛维樱 摄影◎蔡小川
打官司的逻辑
本刊记者到达旧州镇的时候,正赶上“5·28”城隍节。浩浩荡荡的游神队伍,由硕大的木头神怪、孩子、老人各自吹打弹唱的队伍首尾相接,穿越小镇的4条街道。其中戴着面具的地戏队,有特权偶尔停下,在不同的门市小店门口停下唱祷一番,然后骄傲地接下红包。
詹家屯绝不是安顺地区最好找的地戏队。安顺市的简介中“拥有380多出地戏”,现在真正能操练演起来的地戏队,大概不超过30支。游客想听地戏,最方便的途径是在旅游地点“天龙屯堡”提供的地戏片断表演,收十几元可以欣赏十来分钟《三英战吕布》,旁边还配着滚动大字幕。戴张飞面具的曾玉华这一天唱得特别卖力,嗓音激越,打斗时腿脚也快。他告诉本刊记者:“今天下班早,我现在只有周末回詹家屯看看,四五年了都在天龙这住着,唱戏赚钱。”他的晚餐就是一碗辣椒菜汤拌米饭,再有一小杯白酒。作为詹家屯的“神头”,月收入八九百元的58岁的曾玉华现在依然是家里的经济支柱。他说,“在这里不能把自己当艺术家,也就是个打工仔”。
之所以有“艺术家”一说,是曾玉华在今年的官司后,“得了一个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”,虽然补贴一年只有5000多元,“毕竟是领导上重视的结果”。其实在他心里,“艺术家”应该是从1993年去台湾演出开始算的,“那可是人家台湾的大学教授,来安顺转了一个月选的我们这一队”。安顺市的地戏队众多,这里是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的驻兵之地,“屯堡”遍布,操演地戏实为练武,现在老年妇女还穿着明朝服饰,在很多人类学家的描述中这里简直是“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”的桃花源。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,各路地戏队就开始受到不同地区、国家的邀约,前往外地表演,演出最多的三四支队伍中,詹家屯也在其中。“一年到头我们光外国宾客就要接待多少!”曾玉华自豪地认为,“我们也是见世面的人”。
在2004年受到张艺谋《千里走单骑》剧组青睐,被挑选去云南丽江拍戏前,农民们完全没听过“张艺谋”这个名字。“我从来没看过电影,电视都很少看。”他们的日常生活大部分被农活占据。“我们这些屯堡都有个特点,就是封闭。唱戏祖辈上也是自娱自乐的意思,甚至外村的、外姓的都不太来看,我们自己演戏。出去演出都是领导安排的,我们自己也不会弄。”詹学彦告诉本刊记者。
当时剧组委托安顺市前文化局局长在当地寻找地戏艺人。“老局长直接找的我们,把我们带到了丽江,又介绍了很多,我们才知道这是个国际著名导演,跟他拍过电影都能出名。”这时“张艺谋”三个字突然就有了点石成金的功力,“村里的人像着魔一样”。詹学彦也是戏队“神头”。“当时剧组本来说要14人,临要走了突然缩减成8人。”这个变动使戏队出现了分裂,“要去都去,要不去谁也不能去”。詹学彦当时承担的角色,是去扮演唱戏的演员的替身,算是主角了。最后他反复做工作的结果是,回来时给其他没去的人分一些报酬。
在詹学彦看来,自己这一次往外走“成本太高了”:“以往我们去上海或北京演出,都没有参加张艺谋电影这么难。大家连身份证也没有,不少从外地赶回来的,地戏队里虽然我能做主,可是农村人都是爱说风凉话的。”不过詹学彦还是觉得应该去,“电影一上我们必然要火了,地戏不就也火了?”但到了云南,大家觉得有点奇怪,“剧组不让我们带自己的面具和服装”。剧组对地戏的行头已经在安顺精心置办好了,但是演出中只字未提“贵州安顺地戏”之类的字眼。“我们还以为拍电影是去给我们地戏做宣传的,现在想想,怎么可能呢?丽江有钱,人家张艺谋是丽江请的,戏都是在云南拍的,安顺又没出钱,人家凭啥要给我们宣传呢?”詹学彦虽然精明,却并不敢在当时提出自己的意见。他告诉本刊记者:“我一共就见了张艺谋四五次,也没说上话,我们拍戏他是来看的,但是我一个农民,只是个替身演员,脸都露不出,哪能去和他说什么的?都是一些主任、副导演什么的,也不知是谁,反正发指示的都是这些人。”
“后来很多村民说我们卖祖宗,其实我们真冤枉,没有签演出合同,只是给我们每人60元一天的演出费用,我是神头又是主要的,120元。一共待了不到20天吧,还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牢里,说是和犯人一起可以体验生活。”詹学彦说他当时演出非常卖力,扮关云长是他的长项,一切唱词动作都烂熟于心。“我们都被要求和犯人一样,穿犯人的衣服,剃光头。大家都觉得很委屈,可是我们是农民,去和人说我们不愿意,根本没人理。”这些气愤的说辞,并不是因为打官司而临时生出的想法,无论是曾玉华还是詹学彦,谈到要和犯人一起就语气激动,满脸通红。“有一次拍完监狱的戏,我去剧组打饭,可能人家没看出来,还特别严厉地说,你怎么还不回去,你不在这儿吃!”曾玉华说,“我和一个副导演说,我们不愿意剃头,不想和犯人一起,我们又没犯法!人家说,那你自己考虑,这戏还拍不拍?你是个头。把难题丢给我了。我一想不拍不行了,人生地不熟,工钱到最后临走时才给我们,如果半中腰不干了我们一分钱拿不到怎么回去,怎么交代呢?都已经答应了这码事,那个老局长接洽这事也是好意,可是他并没和我们在一起,我们又没有合同,真是委屈得很!”
面具后的表情
詹学彦告诉本刊记者,2006年电影上映,他和地戏队完全不知道,他们从丽江回来时为了缓和队里的矛盾,“买了不少礼物,还把报酬分给了没去的人。拍电影没火受气也没啥的,可是村里人天天在你背后说风凉话可受不了”。直到詹学彦有一天拿到了一张VCD,“一个村里的人给我带回来了,说电影都上了,咋没说咱们村子呢?”果然,电影里15分钟左右的詹学彦戴着关云长面具,与地戏队一起表演的桥段,旁边放的大字幕是“云南面具戏”。在影片结尾迅速上滑的字幕中,詹学彦他们反复慢进,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“贵州安顺詹家屯戏队”的字样。“没说地戏,也没说‘三国’戏队。”因为詹家屯有两大戏队,另一组姓叶,祖传的是《岳飞传》。詹学彦说他这才真正难受起来:“村里人都知道我们去拍了电影,可是却没提贵州地戏这几个字,对于外人来说可能无所谓,可是对于我们,这几个字就对不上了。”
于是村里村外有了许多“卖祖求荣”的辱骂,詹学彦说:“我过了很长一段内外交困的日子。这个电影拍得太亏了,上当的感觉特别强。”不到这些屯堡走走,很难理解到底当地人对地戏为何有这么强的归属感情。翻开上世纪80年代誊抄出来的《三国》老戏本子,上面记录着每一代“神头”在地方上担任的职务。詹、曾两姓是明代来此驻军的将军姓,在战役中曾战死,而詹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曾姓家族,因此两姓定下了“永不结亲”的誓言,也有了按照“桃园三结义”的寓意传下来的《三国》地戏。这样的祖宗传奇是每个村落姓氏拥有一出地戏的精神根源,600年的时间足够一部地戏在一个姓氏里被供奉起来。神头从詹、曾两个将军开始算,职务是“正副将军”,后来有了“武庠”、“府君”、“进士”、“秀才”之类的人,而到曾玉华的父亲曾建章,写的是“区长”。“他在1946年就参加革命了,解放时是安顺县的公安局长,后来又做了区长,一个月40多元工资。到自然灾害时期,因为我弟弟饿死了,他就回家务农,被当做‘擅自离职’处理了。他回家就是唱戏,当神头。”基本上村里最有出息的人,就担当了“神头”。到了詹学彦和曾玉华这里,就没有职务了,但他们的父亲都是神头。“个人在村里非常有威望,我们俩都做过一段时间村委会主任、会计。”说起“跳神”、“神头”,他们自己非常骄傲。
他们更强调自己在本地受到的尊崇。比起曾玉华,詹学彦更加内敛和爱体面。他评上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,安顺只有两人享此殊荣。旅游景点请他去跳,他跳了几个月就回家了,“5·28”城隍节时他说自己“只是个去喝酒的”,根本就不参加演出。“地戏队给各家唱一段,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几十桌酒席让所有人一起吃,礼节太不周了。”他向本刊记者翻开照相簿,“你看过去我们去哪个地方唱一段,至少要有猪头和雄鸡。参庙、参水井、参门楼或八卦图,各种仪式或者喜事,流程是很严格的。”
他领我们去看詹家屯自己的“神柜”,看似破旧的一间房屋里,却要所有人洗了手才能去打开几口大箱子,看那些雕刻繁复又美丽的面具。“一个戏队有一个神柜放这些,这三个面具都有400年以上了,是‘文革’时偷偷留下的。”是黄忠等几个三国将帅,后面的木头已经破碎到反复用黏合剂粘过,而漆色形状都很有神韵。“每次唱戏都用,一两年就修一次。面具使用前一定要用鸡血点一下额头。这些面具太老了,我们得像对祖先一样敬着。”几个妇女离个三五米以外在看,让她们过来她们就连连摆手。“女人尤其是带孩子的女人绝对不能碰面具,她们身上有奶气,都阴气太重,老辈人就说她们被面具惊到。”
地戏在当地绝非“戏班子”,而是代表祖宗神仙。“你戴上这个面具,你就得做出老祖辈们的样子了。”詹学彦说他从9岁就跟着父亲唱地戏,“谁家请我们去,都是特别隆重的仪式,要街道里摆出香案,他们本村也有会唱的,就开始给我们出题。比如香案上放马,我们就得唱马超;布里包一个铝块,就得唱吕布;还有放块糖的,那是唱四马投唐。谁家考学高升,谁家求子,我们还有很多小段子可以唱,现编也没问题,唱对了他的心思,一串鞭炮把我们送过去。这才是待客之道,至于红包、酒席和各种费用更不用我们说。”现在的仪式只要主人家摆个香案,主人在前面鞠三个躬就完事。“在自己村里唱戏更隆重,每个村各唱各的,也有打擂台的,今天唱到哪出戏,暗合哪个姓氏,本门就风光。第一天不能唱,要杀鸡、扫场、坐朝。”本刊记者没弄懂“坐朝”的意思,曾玉华激动地说:“北京有天安门没有?那就是朝,那就是规矩!”
氏族与地戏
安顺的詹姓都由詹家屯源出,传说里朱元璋带来的24姓人家,现在已经演化成极大的氏族。“1989年的时候,还有180多支地戏队参加地戏大赛。每村每姓一戏,可想而知多么壮观。然而那一次就是最后的繁盛了。”曾玉华的父亲曾建章当时还担任了地戏大赛的评委。而在詹家屯的记忆里,除了这次和张艺谋打官司,那次是最深刻的“眼泪都要掉下来”的经历。詹家屯有三大姓氏,除了詹、曾两姓世代交好,还有叶姓唱的是另一出。“我们平时都结亲的,但是一到跳神的时候,谁也不搭理谁了,这么多年的默契是,谁也不评论谁的戏。”叶家人都知道詹学彦惹的官司麻烦,但是他们的祖训是,“绝不能评论人家的戏,矛盾太大了”。
有趣的是,几个姓氏的老人都特别乐于回忆1989年的地戏大赛:“看起来只是为了丰富文化生活的比赛,实际上是所有大姓之间的争斗。”“文革”并没有摧毁地戏,相反,大多数村寨都有老人凭着记忆或偷藏下来的戏本子,恢复了“跳神”。“一部《三国》跳下来要三个月时间。”詹家屯的《三国》戏本有八册,用蝇头小楷抄写,字体也不一样,每句以七字为主,也有少数十字的,用来回忆,像回放镜头一样的叙事。詹学彦说着就唱起来,他非常推崇里面张辽说关羽降曹,字词都很美。尽管唱戏的人文化程度都是小学未完,却能背下许多词句,用语简洁易懂,还有“战袍磨得风烟起”之类的形容,詹学彦说,“80年代我们唱之前每天要排练,先点将,谁扮什么,然后不拿本子,互相唱,最后走场操练,这样几个月才上台演出。来晚的人还会被很严厉地训斥,有家规。老中青都有,现在我们队还有几个20多岁的人唱”。
当时这个戏队在大赛初选时得了詹家屯最高的分数,“当时詹家屯是个大村,有五六个大姓,所以有五六台地戏。”可是到了汇演时候,这支队伍却落选了。詹、曾两姓说:“是叶姓的一个人在旧州做宣传的,他动了手脚,把我们拿掉了,叶姓的《岳飞传》就参加汇演去了。”曾建章当时做主让詹、曾唱地戏的30多口人,“背着干粮,带着行头,住在安顺县里的一个村子,住了十几天,就是为了去县里头告状”。在詹家屯乃至安顺市,那场官司当时的影响不亚于这次。“我们找了当时的一个副县长,她去查了我们的分数,确实是最高的。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参加汇演了,那次是贵州省拨款,第一次做地戏的调研。”关于当时的情况,居然有这样一份报道,在前面的官样文章后记叙:“大赛进行到最后一天,比赛现场出现了骚动。演出现场突然挤进了一支队伍,要求参加比赛,一时场面陷入混乱……”
“因为叶姓做了手脚我们不服啊!一个杂务跑进会场喊‘你们办事不公道!’”詹学彦现在讲起来还是难免激动。“我那时30多岁,上面还有一辈人给做主。治安的人要抓这个杂务,我们当时真是豁出命去,也要保住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名誉。”詹学彦现在的回忆已经很美好了,“当时领导听我们唱完,都说重新打分,给了我们一个最高分,我还记得是97点多。那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时刻。”而曾玉华记得,“还是交了200元,才让我们表演了20分钟。不划算也得争啊!”
他们说,那时县里已经连轴转演了三天,“评委们精神疲惫、不以为然”,但詹学彦上场踢枪、飞脚、抓雉尾,接着唱起来清亮高亢。“马超见曹操逃了,枪尖却扎在树里拔不出,他又拖又拽,狂叫不已……”当时报道的描述把演马超的詹学彦形容为“如情如心”,也因为这样真正发自内心的表演,詹家屯三国戏队得到了第一个公认的荣誉。“当时大赛排名已经出来了,我们只好给个特等奖,叶家的《岳传》是二等奖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。叶姓有人原来是部队里的文书,叶家也比较有文化,在本地政府有不少人,“我们詹、曾有习武的传统,不大读书的”。
“后来举办的比赛也好,邀请哪个戏队出国也好,其实越来越有经济的成分了。”詹学彦有点黯然地说,“如果还按照自家唱自家,我们才是原汁原味的,毕竟各家的戏本子还是不太一样,演员的风格味道也不同。可是现在受经济冲击了,和我们原来唱的初衷已经不同,完全违反地戏和家族的关系。”
吃一“堑”长一“智”
因为《千里走单骑》寻找“面具戏”的人,基本上找不到贵州来,因为丽江当地早已率先打出了“云南关索戏”的演出招牌,并且以这部电影为卖点。“一个老师告诉我,他去看了一场,就给了1000块钱。”詹学彦说。关索戏和地戏很像,只是面具的感觉不同,外行人特别是游客也不会追根问底。不平是一回事,詹、曾两姓再怎么要说法,也没有能力真正和张艺谋对簿公堂。这场官司的原告是安顺市文化局,詹、曾等当时参加电影的演员,只是作为证人出庭而已。“如果政府不出面,我们不可能打这个官司。因为政府知道了以后也很恼火。”上一场官司也只是到官员面前争个名分,“这次不一样了,2007年那会儿政府就告诉我们,张艺谋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导演,我们得从大局出发,不能在这时候给人家惹事”。
从聘律师、搜证到整个官司的程序,地戏队完全不了解状况。“这些我们都得听政府的,不然谁来告诉我们呢?”詹学彦说,“张艺谋拍片我是觉得非常敬佩非常好的,可是他拍地戏这段不对,不是以我们为主,是以他电影的故事情节为主的,怎么拍地戏他还是个外行。”他给我们用影碟机,放了一段他们自己演绎《千里走单骑》这一整段“过五关斩六将”的录像。在村头的草坪上,他们各自戴着面具,在画面里卖力地做出各种姿势和打斗动作,还有配着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音乐的片头,虽然画面粗糙,但那种原始质朴的认真和努力让人感动。詹学彦感慨地看着说,“有一个里面的演员已经不在了”。
现在最常挂在他们口头的一句话就是“受到经济的冲击”。詹家屯没有旅游优势,只能凭真本事吸引各种来观看的人,“大部分是领导安排的,让我们接待,我们就演一场,领导有时会给我们一些劳务费什么的”。这样的活无论多少他们还是觉得很光荣,然而普通的来访者则不一定了。詹学彦一开始说,“为了电影官司的事来的,我们都不会收任何费用”,然而最后一天采访拍摄时,曾玉华却说,“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,耽误了自己的收入”,坚持收取一定报酬。对于詹、曾两家,他们说,“我们不需要用张艺谋炒作,我们已经很有名了”。不过碍于尚未从制片方得到答复,当地并没大张旗鼓地以电影为噱头来宣传,导游也只是顺嘴一提。“非物质文化遗产嘛,就不得物质了。”曾玉华说,“政府打官司不过就是求个名,我们呢,说实话,我们演那个电影钱太少了,可是领导不愿意让我们说这一层。”
以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名义打这个官司,而“非遗”并没有专门的保护法。张艺谋的代理律师佟洁说,“非遗的保护法规是否会设立知识产权,它的性质、范围是什么,谁来主张这个权利等等,目前都没有结论。也就是说,原告主张的(在影片《千里走单骑》中对安顺地戏的)署名权,没有法律依据”。原告提出的要求包括停止放映影片和提出道歉,“不过如果能够给贵州地戏正名,也可以继续放映”。另一方张艺谋的剧组只有律师出庭。“绕来绕去,就是不回答我们的问题,我们其实就一个问题,你就说这是不是贵州地戏?张艺谋口中承认这是安顺的就好,他不正面回答,还有法官呢,法官回答也行。这个道理我觉得还是说得下去。”詹学彦说。
“我估计张艺谋是世界的、国家的著名导演,也不可能把他怎么样吧,估计最后就是又要恢复我们的名声,又不给他造成不好的影响。”詹学彦的精明再次显示,“说实话,安顺以前不重视我们地戏,现在是给电影搞出了名堂,才又来管了。原来光顾着让我们贡献贡献,其实地戏本来是应该被保护、尊重的。不说我是艺术家,不按演员说,就是我是农民,还有一天最低误工补助60元钱。去给镇上演出一个红包才块八毛钱,我们开香祷告祖宗都不够。一个戏队至少也得十五六人的,现在都是老人,长坂坡83万人拿什么演呢?”詹学彦的梦想是把村里的学堂老房子修好,现在那里有个石头戏台,“应该矮一半才好,”屋子里都是蒙尘的地戏奖状、锦旗之类,“我们也好有个地方演。”
新浪独家稿件声明:该作品(文字、图片、图表及音视频)特供新浪使用,未经授权,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。